
【内容摘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并在全社会广泛应用,其中也包括艺术创作。形形色色的人工智能画家挑战着人类艺术家,并引发了众多争论。本文从技术史、艺术史、人文主义三方面综合探讨人工智能绘画的现状与前景。从技术逻辑来看,人工智能画家要创作出能与人类大师相媲美的艺术作品并非难事;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通过既有数据学习来进行创作的人工智能画家要创造全新的艺术范式则很难;而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人类社会仍建基于人文主义,人工智能画家就不可能取代人类画家;最后,远瞻未来,也许随着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能成为碳基和硅基融合的“新人”,艺术也会成为相应的“新艺术”。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 艺术 绘画 技术史 艺术史 人文主义
人工智能的历史很长,其正式被提出业已六十余年,但它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时间却并不长。近些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技术的突破,尤其是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接驳,使得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被取代,展现出在工业、农业、医疗、汽车、电商、游戏、物流、传媒等众多领域的广阔前景。人工智能绘画也是这样的产物,并迅速在艺术界引发热议,譬如,人工智能绘画算不算真正的艺术?人工智能绘画是否代表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绘画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类画家?
马克思曾说,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如果人所生产的工具脱离人类的控制并自行其是,就会引发重大的人文主义危机。2022年OpenAI公司发布ChatGPT,2024年又发布了Sora,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快速进化的趋势,使得人类在叹为观止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强烈的危机意识。同样,人工智能绘画机器人的进步也使得人类艺术家深感不安。本文尝试从技术史、艺术史、人文主义的综合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技术史视角
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在其著作《自然史》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绘画起源的故事:一位柯林斯姑娘的爱人即将远行,为了留住爱人的形象,姑娘通过火把照射他在墙上形成的影子描摹下了爱人的形象。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这个关于绘画起源的传说成为不少画家钟爱的题材。这不仅让那个忠贞的爱情故事得以流传,也引起了研究者对绘画本质的讨论,尤其是在摄影术出现之后,这个奇妙的故事和那些相关作品激发人们开始重新评估非人工手段和机器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和价值。2001年,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隐秘的知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观点,15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史中满是使用光学设备辅助进行的绘画创作(图1),这似乎成为了普林尼关于绘画起源故事中技术手段在艺术创作中重要作用的另一个注解。

图1 画师使用测量设备绘制肖像 丢勒《测量指南》木刻插图 13×14.8cm 1525年 大英博物馆藏
正如霍克尼所指出的那样,在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进程中,技术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除了光学辅助设备,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机这种被视为“改革动因”的新发明也直接催生出版画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工业革命以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与技术进步和媒介革新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从印象派到装置艺术,从录像艺术到互联网艺术,这一趋势极其明显。但其中发挥作用的新技术并不仅仅是视觉机器,也包括许多生产新艺术的必要物质技术条件。如果没有现代光学、化学工业、铁路网络……很难想象印象派的产生;如果没有规模化生产、流水线作业、围绕都市建立的现代生活方式,恐怕就不会有装置艺术;如果没有商业电视网络、家用录像机及播放设备,也同样不会出现录像艺术。
或许,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上的运用,可以被视为艺术发展的技术史的最前沿。其基本原理如下: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基于对人类神经网络的模拟,随着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步,以及对人类脑神经运作原理的进一步明晰化,利用技术模拟神经元网络的科学程度和效率持续提高。其次,其技术实现高度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其一是运算能力的提高(硬件),其二是算法设计的优化(软件)。最后,这些技术还需要占有大量的数据,从最初由人类筛选和投喂特定数据来训练模型,到深度学习,再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进行自主学习,数据问题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上述几方面的很多技术创新都是在21世纪才取得了突破,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虽然历史很长,但直到最近十年才在社会层面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开始,人工智能挑战的对象总是下棋,这一历史从1914年西班牙工程师莱昂拉多•托利斯•克韦多(Leonardo Torresy Quevedo)创造第一个自动下棋机就开始了,但大众更熟悉的可能是IBM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深蓝(Deep Blue)和Google旗下DeepMind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前者在1997年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Гарри Каспаров),后者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和柯洁,从此人类棋手再也难与人工智能棋手一较高下。人工智能之所以在长达百年的实践中一直执着于下棋,是因为下棋是一项既复杂又简单的工作。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它除了尽量多和快地计算可能性外,不再有其他任务;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它需要很强的运算能力和巧妙的算法。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开始挑战艺术。艺术比下棋要复杂得多,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艺术中蕴含着人类的“体验”“情感”“创造”等“不可取代”的因素。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者和开发者而言,“体验”“情感”“创造”等也是数据和算法,只不过相对于下棋而言,这无论是在神经元网络原理研究方面,还是在运算能力和算法设计方面,都不在一个层级上。每下一步棋、每落一次子,计算机都会计算其背后的各种可能性,尽量降低其偶然性;对于机器而言,人类的体验、情感、创造也是“可能性”,它们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不可模拟的,是因为其可能性太多、太复杂,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但这取决于脑神经科学的发展、运算能力的增强和算法的科学程度,如果脑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突破、计算机足够强大,模拟人类的体验、情感和创造并非不可能。
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展现出这方面的潜力,尽管仍然不够成熟,但微软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诗人小冰、Google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画家深梦(Deep Dream)、罗格斯大学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导开发的人工智能画家CAN(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等,不仅拥有高智商,而且拥有高情商。后者不但通过了图灵测试,而且在该测试中,53%的人工智能绘画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图2),对照组(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的人类画家作品)的认同率仅有41%,在创新性和复杂性等关键指标上,人工智能绘画也高于人类画家的作品。因此,鉴于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快速进化,从技术逻辑及其前景来看,人工智能画家完全可以和人类艺术家做得一样,甚至更好。

图2 CAN在学习后“创作”的抽象绘画作品,The Art & AI Laboratory, Rutgers University
二、艺术史视角
在上述实验中,CAN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主要是抽象绘画,图灵测试的对照组所选取的作品则是当代艺术家的抽象绘画,尽管CAN“打败”了当代画家,但是,在将对照组换做历史上抽象艺术大师的作品时,CAN则完全处于下风,人类大师仍以85%的优秀成绩碾压人工智能。新闻报道中常常用“创造历史”来形容人工智能所取得的成绩,然而,“创造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艺术而言,这意味着它会被未来的艺术史所记录,甚至改变艺术史的走向。尽管艺术史也是一部技术史,但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试图使用新技术创作的艺术都会被艺术史所记录。新技术不是艺术史评估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唯一指标,而是复杂指标系统中的一种,甚至是并不一定必要的那一种。
可以这样来看待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是一座高山,艺术大师们和他们创造的代表性作品处在这座高山的顶峰,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的时代构造出一个由许多高山绵延形成的山脉,将绵延的高山的顶峰连接起来,就成就了一部艺术史。然而,这种描述还不够,因为,不同高山的顶峰在性质上并不相同,甚至充满了断裂性,正如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所言,“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是艺术,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是艺术,智利复活节岛的巨型石像是艺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图3)是艺术,日本武士的精美铠甲是艺术,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中产阶级生活是艺术,毕加索创造的撕裂形象是艺术,杜尚的小便池现成品《泉》(图4)是艺术,人工智能艺术也正在被试图看作是艺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显然不是因为半坡陶罐和杜尚的《泉》都是陶制品。大胆想象一下,如果可能,当达•芬奇看到《泉》时,他会如何判断?当马奈看到人工智能绘画时,他会作何感想?

图3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混合材料壁画 460×880cm 1498年 米兰感恩圣母院

图4 杜尚《泉》小便池现成品 1917年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 摄影
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地阐述了一个论断,即科学史不是一个知识累积和推翻的直线增长过程,而是一个“范式”(paradigm)不断转型的过程。所谓范式,就是一个时代具有共识的科学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科学的历史。与之相似,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与“范式”具有极强可比性的“知识型”(或“认识型”, L’épistémè)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型是一种“匿名的历史规则”,是一定时期内关于“知识”的基本共识。知识型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时过境迁,知识型就会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就是知识转型。不同的知识型和知识转型的过程,构成了人类知识史或认知史的前提。
艺术史也可以被看作是范式或知识型不断转变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革命”,而不是“美”或其他固定逻辑的直线发展。当然,如果这样,艺术自身也不存在某种内在的本质和自律性,而是随着范式转型而不断变化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被奉为艺术史中的经典之作,是因为他画得好?具有创造性?或是表达了真情实感?“最后的晚餐”是艺术史中的常见母题,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期,基督和12名使徒常常被描绘为围绕长桌或圆桌而坐,背叛者犹大一般被设计为背对观众、手拿装着出卖基督所获金币的钱袋,而基督和其他人则坐在桌子的另一侧,譬如安德里亚•德尔•卡斯塔诺(Andrea del Castagno,1423—1457)在1447年绘制的《最后的晚餐》(图5)。

图5 安德里亚•德尔•卡斯塔诺《最后的晚餐》湿壁画 453×975cm 1447年 佛罗伦萨圣阿波罗尼亚修道院
这件作品是文艺复兴早期向盛期过渡的作品,既带有文艺复兴艺术的特征,又显示出中世纪艺术的强烈影响。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相对孤立,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就像13张单独的肖像画拼凑在一起。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则不是这样,包括犹大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安排在餐桌的同一侧,人们被划分为几组,戏剧性地展现了基督告诉大家自己被出卖,而出卖者就在眼前的复杂情景。这两件作品的差异不仅说明了艺术自身的调整,也展现出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卡斯塔诺《最后的晚餐》具有强烈的示意性,对《圣经》进行了相对简单的图解,原因之一是反对偶像崇拜仍无处不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则要世俗得多,构图充满了视觉性、叙事性和戏剧性,人物刻画也更加真实和丰满,这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剧变。
人工智能画家高度依赖于对数据的学习,这些数据都是即有的,换言之,人工智能画家是在某种业已存在的范式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并创作的,它的创作难以逾越它所学习的那种范式。CAN的例子说明,人工智能画家可能在学习大量人类抽象绘画的基础上超越很多人类画家,但与那些开创抽象艺术范式的经典相比,仍有差距。如果人工智能画家学习的是卡斯塔诺那样的《最后的晚餐》,它就无法创造出达•芬奇那样的《最后的晚餐》。不过,眼下的技术逻辑很清晰,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艺术要和那些经典做得一样好,并没有太多障碍。然而,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预测范式的转变吗?能够创造出一种真正全新的艺术、为未来的艺术立法吗?能够被艺术史记录甚至改变艺术史吗?
对于人类而言,范式的转变充满无数偶然,几乎不可预知,就像牛顿无法预测爱因斯坦、达•芬奇无法预测杜尚一样。但在计算机的词典里没有“偶然性”,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只不过“偶然性”意味着更多、更复杂的可能性。要对下一个艺术范式进行预测,就必须对社会整体变迁作出预测,其中也包括对技术自身命运的预测。譬如摄影术的出现,使得画家能够描绘“瞬间”,从而产生了大量不稳定的构图和形象,但人类却因此改变了艺术的“游戏规则”,从此,极尽写实之能的绘画被新艺术淘汰,艺术范式更迭,从此走向了现代主义。这样的计算很难,这不但意味着人工智能必须要超越人类,还要超越上帝,成为几乎能够计算一切的超级人工智能。不过,技术在加速进步,并日益强烈地重塑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因此,可能性依然存在,结局仍是开放的。
三、人文主义视角
人工智能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它能改变人类的历史、创造人类的未来吗?一方面,这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类的自我认知。人类的自我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不断演进的。人曾经被视为是神的造物,一切听从神、服从神就好。文艺复兴以来,人开始学会遵从自我的意志,人文主义由此开启,并逐渐成为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直到现在。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在1940年提出了“机器人三原则”,包括: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冲突;3.在不违反第一条和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尽管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但前提是保证人类的安全。
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叙述了复制人在暴动之后被人类杀戮的故事。复制人在生理上与人类一模一样,但他们不是“人”,不拥有人类的权利,一旦威胁到人类的安全,就必须被消灭。类似的情节在科幻片中屡屡上演,生动地展现了今天的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可以想象一下,在极端的情况下,如地球毁灭时,人类乘坐宇宙飞船逃离地球,在茫茫宇宙中寻找新家园的情景——人类在肉体上的存在是人文主义的底线,无论威胁人类存在的是天灾还是人祸。生物克隆技术在今天已经很成熟,但克隆人不但被神学家反对,也被主流科学界反对。因为,这与承认人工智能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一样,将会导致重大的人文主义危机,从而瓦解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
2017年,《救世主》(图6)被专家鉴定为达•芬奇原作后,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4.5亿美元成交,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画作。该作曾被鉴定为其学徒制作,1958年仅以45英镑的价格出售。时光流转,作品自身并未发生任何物理性的变化,为何在被确认为达•芬奇原作后价格飙升了80万倍?关键就在于,这件作品被认同为由达•芬奇“本人”所“原创”。在这个案例中,“本人”和“原创”,二者缺一不可,且彼此关联——伟大的艺术家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杰作,今天的我们都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这件作品是达•芬奇对前人的仿作或匿名艺术家的原创,其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匿名艺术家的仿作。宗教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个人”和“个性”的迅速崛起,艺术家不再模仿前人的画作,而将主要目标定位在“原创性”(originality)上,《救世主》价格的飙升展现了人类对艺术认知的现状。

图6 达•芬奇《救世主》木板油画 66×47cm 约1500年 2017年11月15日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售出,私人藏
梵高也好,高更也好,无论他们的作品如何离经叛道、偏离前人的经典,都会在“创新”的全新标准下被接纳和认可,这也反映了人文主义进入到新的阶段。1917年,杜尚在小便池现成品(ready-made)上戏谑地签名“R.Mutt”,并送独立沙龙展,结果遭到拒绝,没人知道“R.Mutt”是谁,也没人能够确认一个小便池现成品的艺术品地位。但是,在杜尚的作者身份公开后,本来反对该作展出的展览组委会成员凯瑟琳•索菲•德雷尔(Katherine Sophie Dreier)改变了主意,接受了这件作品:“我接受的现成品是能够在其组合中显现艺术家原创性的作品。”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E. Krauss)也曾指出,“在前卫艺术家目不暇接的语境中,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他们一直坚守——原创性”,并且,“艺术家自身的独特性确保了其作品的原创性”。
尽管“原创性”可以从主题、题材、风格、形式、媒材等方面予以评估,但更为根本的是其背后隐藏的人类和个人的存在——真正的艺术,必须由真正的人所创造,由艺术家亲笔创作出,经历岁月的洗礼。当我们在欣赏艺术时,常常会猜测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他试图通过创作对自我情感的表达,都是由于受到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人们赞赏那些 “英雄式”的现代艺术家,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充满“个性”的现代艺术,这不仅是对其作品的肯定,更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确认。现代科学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是基于人文主义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不同时代,艺术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内涵、物质形态和视觉样式,它们之所以都被冠以“艺术”之名,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在每一个时代,艺术史的范围以及看待过去艺术的方式亦大相径庭,但今天的人们却将它们统统纳入艺术的领地,并创造性地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历史联系。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更迭,更是因为人对自我和艺术认知的变迁。
人们不会在中世纪艺术中寻找“人性”,因为在中世纪基于人文主义的现代社会尚不存在;达•芬奇的艺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人文主义的崛起,却没有任何艺术史家试图在他的艺术中寻找“情感”,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是大写的;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个人”“个性”“原创”成为艺术的新准则,从前艺术史中被传为佳话的借鉴,转而成为被深恶痛绝的抄袭,因为一件作品的背后是著作权,著作权的背后是人权,人权的背后是某个人真实的存在。也许人工智能艺术能够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相媲美,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在以人文主义为基石的社会中,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这不是创作好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类存亡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战争不使用核弹、科技要讲伦理、艺术要追求原创?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建基于人文主义。
四、余论:成为新人
人工智能正以日新月异之势进化,从技术逻辑来看,人工智能画家达到人类艺术大师的水平指日可待。然而,艺术史却并不会轻易接纳人工智能艺术,因为,尽管艺术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但技术的进步却并不一定会推动或改变艺术史的进程。艺术史充满了断裂,它随着人类社会的转型而不断变化其范式。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并非是线性演进的,而是充满了革命。人工智能艺术可以通过对即有数据的学习,在即有艺术范式的标准下创作优秀的艺术作品,但要预测和创造未来的艺术范式,则需要它掌握这个世界业已存在的全部数据,并能计算一切。在可预期的未来,这一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难度极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艺术也好,艺术史也好,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它们统统建基于人类社会,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现代社会的基石——人文主义,决定了真正的艺术必须由真正的人所创造,这是根本性质的问题,与技术毫不相干。
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创作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信仰科学,并热衷于研究生命起源。他终日埋首于实验室,通过对偷来的人类肢体进行组装,制造了一个身高超过2.4米的人工生命,但这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吓坏了弗兰肯斯坦,让他落荒而逃。在随后的故事中,从弗兰肯斯坦的角度看,“怪物”杀害了他的弟弟,对人类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但从“怪物”的角度看,他逐渐熟悉了人类社会,不断成长,甚至学会了人类之爱。后来,他们之间达成了短暂的平衡,“怪物”理解了人类对他的恐惧,希望弗兰肯斯坦为他制造一位同样的人工新娘,并承诺远离人类文明。弗兰肯斯坦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最终却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样会产生一代又一代的“怪物”,遗患无穷。最终,弗兰肯斯坦的妻子在新婚之夜被“怪物”杀死,他自己也在寻仇过程中丧身北极,“怪物”则以自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它让我们不断思考人与人工生命之间的关系。那么,相信人文主义?还是相信后人类主义?《机械战警》创造了一个半人半机器的超人,帮助人更好地实现了人类的正义。《绿野仙踪》中铁皮人总想拥有一颗人类的爱心,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理想。人类需要机器之力,机器需要人类之爱,尽管现实不是童话,但它们仍然展现出了积极的前景。人文主义是我们当今社会牢不可破的基础,但是历史地看,人文主义并不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如果它曾经不是,未来一定会是吗?如果人与机器合二为一,如果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无需必取其一,我们都会成为“新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既是“机械战警”,也是“铁皮人”。而艺术也会成为“新艺术”,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既是人类艺术,也是人工智能艺术。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19世纪,是一个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被视为逐渐走向“异化”的时代。然而,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我们和我们的艺术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盛葳 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期(总第112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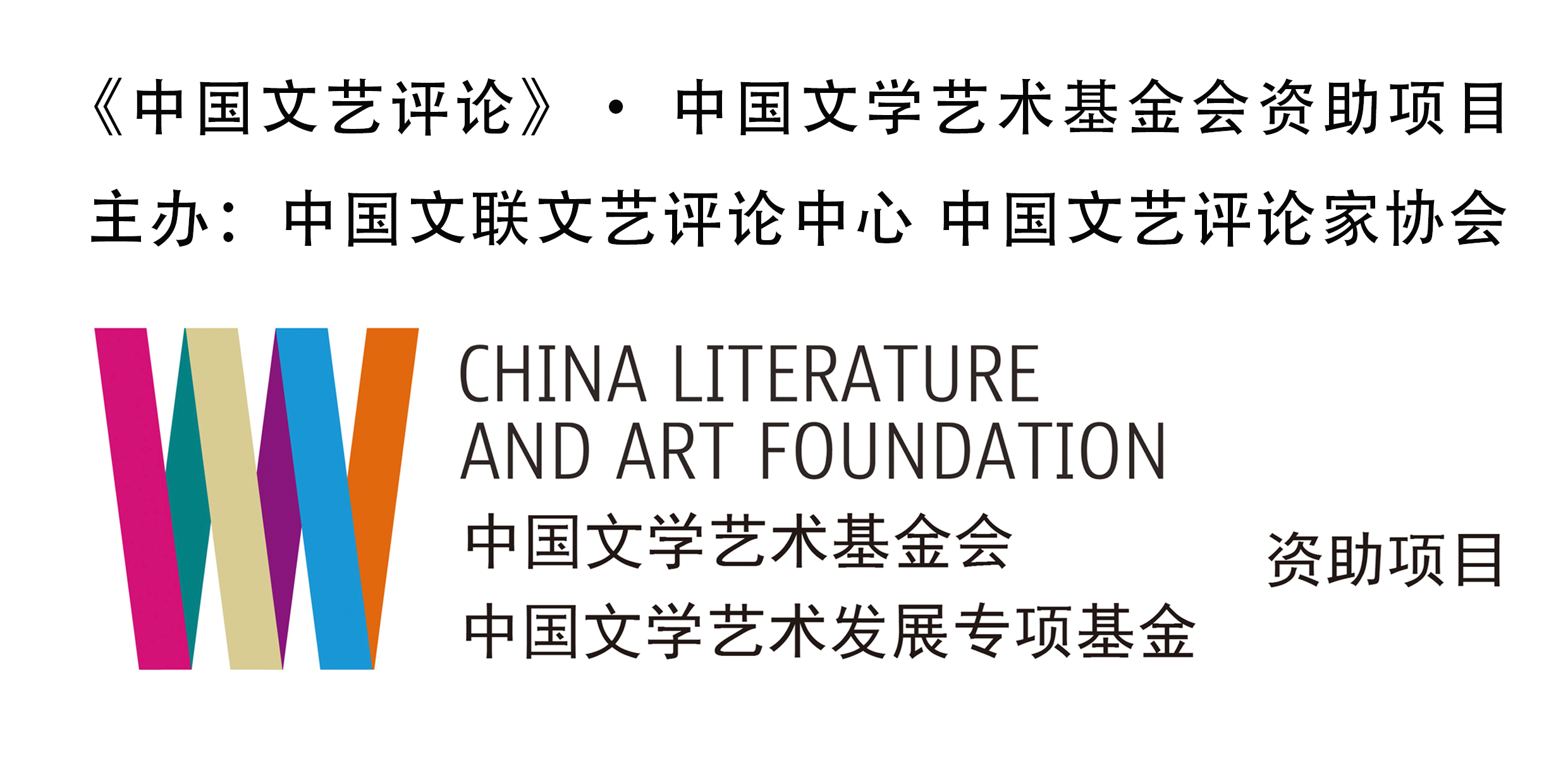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