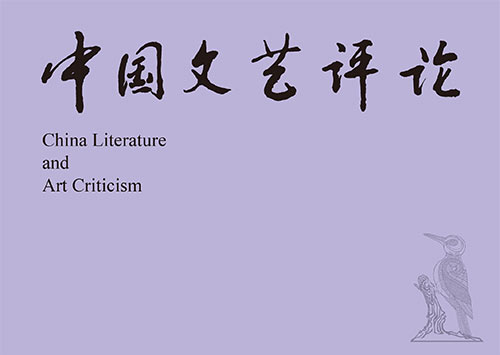
内容摘要:《二子乘舟》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挖掘抢救整理传统剧目”扶持复排的唐派(唐韵笙)名剧,该剧创作于1935年,其时是一部悲剧意蕴浓郁的京剧新创作品,与京剧传统创作格调迥异,该剧的复排展示了“创造性”在京剧传承与创作中的独特价值。
关 键 词:京剧 唐派 《二子乘舟》 复排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在2016年底与福建省京剧院、吉林省京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沈阳京剧院、上海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等单位签署协议,共同启动首批“挖掘抢救整理传统剧目”项目,以此作为京剧艺术传承和保护的重要举措。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入选项目中的《赠绨袍》《南界关》《朝金顶》等就先后复排演出,并且在晋京展演中备受好评。这一挖掘整理工作的成功推进,正说明了京剧乃至中国戏曲诸剧种中,有太多的艺术遗产亟需挖掘传承。近期在北京演出的唐派名剧《二子乘舟》即是一例。
沈阳京剧院挖掘传承的《二子乘舟》,是唐韵笙先生在1935年的新创作品。故事着力展现春秋卫宣公时期的伦理混乱、时势动荡,塑造了一个强权者卫宣公,两位女性宣姜、夷姜,三位公子急子、公子寿、公子朔,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同时通过渲染卫国、宋国、齐国盘根错节的政治瓜葛,强化了卫宣公之子伋子(京剧作“急子”)与公子寿在最终被害时凸显出来的忠孝仁义,显示了2000年来被不断张扬的儒家正统观念理想的文化价值。《诗经》中有《新台》一诗所谓:“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新台有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渔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用强烈的对比反差,讽刺了悲剧的重要制造者卫宣公的伦理错乱;同时有《二子乘舟》一诗所谓:“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暇有害”,用深切的哀婉,对伋子和公子寿的无辜被伤害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情感都成为戏曲在展现这段故事时的重要艺术基调,渗透到了舞台艺术形象中。特别是经过周仲博先生再次改编传习的这部戏,对于宣姜在悲剧中的推波助澜给予了消减和删除,这也对历史上评价宣姜所谓的:“宣纵淫嬖,衅生伋、朔”;“淫纵不简”等观念判断,给予了纠正,显示了对于时代乱局制造者的重新定位。
《二子乘舟》是唐派的老戏,但却是属于时代的新作。对于唐韵笙先生的创作背景与艺术动机尚需考证,但是其题材选择与主题立意却迥异于京剧乃至中国戏曲文学的主流传统。宋元以来的数百年戏曲史一直以文人创作最为突出,而文人创作在杂剧、传奇的基本范式基础上,更多地偏重对于通常伦理价值的表达,以及对于合乎正统主流评价标准的艺术形象的塑造。这也造成了在中国戏曲的古典时期,悲欢离合交织的正剧和喜庆团圆的喜剧,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悲剧。诉诸于民间视野与情感的戏曲创作,在清代地方戏勃兴的时期里,才更加多样地展示着戏曲“热耳酸心”的活力,张扬与古典戏曲绝不相同的艺术道路。尤其是在中国进入现代的文化转型进程中,戏曲在时代文化的引导下,有了更多的创作途径和艺术品位。显然,《二子乘舟》从其结构、表演和主题所具有的现代意义,都毫不逊于莎士比亚经典悲剧,这当然是立足在面对复杂历史时,该剧用古典形式来接续极具现代质感的悲剧书写,所展现出的时代与艺术进行互动提升的艺术实践。
该剧用京剧行当的鲜明个性,给隐蔽在历史中造成社会动荡的王侯们以极大的理性判断和人文标识,剧中卫宣公强娶夷姜、宣姜的乱伦直接造成宫廷悲剧,公子朔搬弄是非成为罪恶与悲剧的推手,戏曲不再延用历史典籍对于宣姜的批判态度,而是用净、丑行当的限定,将历史的底色予以展现。这正是中国在结束千年封建制度后,戏曲在塑造历史人物时,用演义故事张扬新的历史观、人文观的结果。对于历史的重新发现,正与现代中国的艺术进程同步。

图1 《二子乘舟》剧照 (沈阳京剧院提供)
唐韵笙的这部新编作品在极具历史深度观照时,通过急子、公子寿这两个形象的创造,让历史悲剧浓缩成了一个混乱无序时代里个体英雄的命运悲剧和个性悲剧。剧终之时,公子急与公子寿在吟唱着“酒中泪可算是滴滴情厚,兄饮这泪和酒铭记心头”,展现了徘徊于纯粹的道德理想与黑暗的社会政治之间的人性坚守与生命陨落。被自私贪婪所毁灭的清白理想,最终浓缩在“用尽伤心曲,听得江水悠”的古今感怀中,这种意蕴显然不同于大团圆式的中国传统故事,而是以急子与公子寿的相互理解和共同毁灭,彰显了传统人格的尊严价值。剧中的急子是一个仁义贤孝的公子,他的所有隐忍显示了他对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尊奉,对于父亲的筑台纳媳,他气急倒地却最终遵从父命而赴边疆守卫16年;对于已经成为母后的宣姜,他谨守礼仪,用归于平常的心态来避免外人讥议;甚至对于被赐死的母亲夷姜,他只能用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来选择进入卫宣公与公子朔设计好的圈套。这些作为都是他所认定的“自循宗法”的行为,也是一个生活在纯粹道德规范里的贵族公子良好的生活态度,正与他在卫宋战争时用“仁义”而非杀戮来宽宏大度地面对宋国挑衅是一致的。但是,他的仁义在无义的春秋乱世中,却遭到了最残酷的毁灭与无视,甚至在卫宣公的仇恨与忌惮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横亘在他的悲剧之上的,正是世风日下的道德沦亡,这正与他以仁义为追求的理想道德背道而行。而为了保护兄长、挽救卫国命运的公子寿,也成了这场悲剧里与急子一样的殉难者。兄弟二人的单纯正义成了历史文化长河里的一股清流,虽然被时代所淹灭,却长生于文化前进的正道洪流中,辩证地显示着脆弱的人生中不可遮蔽的文化力量。如果站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立场,急子与公子寿看似迂腐的作为正显示了他们的道德坚守;如果站在颠覆传统的现代社会,急子与公子寿看似没落的作为则显示了他们的文化坚守,都因为悲剧的结局而具有了多义性的解读价值。当然,这正是特殊的时代里的现代理性精神凝聚其中的结果,正是悲剧在京剧现代创造史上的重要成果。
该剧人物关系复杂,重新整理后的剧作开场即将公子急与宣姜的婚姻摆在面前,两人路上相遇,在计议如何处理讨伐宋国与缔结婚姻时,埋下了个性悲剧与命运悲剧的走向。第二场卫宣公新台纳媳,浓重渲染了色厉内荏的宣公污损道德人伦底线的政治悲剧。紧接宋、卫战争之后的第四场,即进入16年后公子寿、公子朔的人格反差以及颠倒的宫廷生活,彰显的是完全混乱无序的社会悲剧。这些渲染随着急子与宣姜的新台会晤,彻底暴露出以死亡与血腥为特色的终极结果。情节层层推进,人性的善恶紧紧纠缠在彼此错乱的关系中,让人的选择在被动的环境中彻底毁灭。特别是该剧中的急子,融汇了生行在老生、武生、文武老生的表演,实际也跨越消减了行当的界限,走向了人物形象的多元展示,文武兼备,唱做并重,用凸显人物内心的塑造技法成功展现了力量与道德兼美而命运悲情与性格相彰的独特艺术形象。这种情节、结构与形象的与众不同,正是京剧在从近代以来花部戏曲创作范式,走向了现代意义的文学创造的重要见证,这显然是京剧与时俱进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内容。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展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性的深度张扬和对于现代性的艺术赋予,那么以《二子乘舟》为代表的戏曲创作展现的同样是戏曲进入现代创作之后,从恪尊道德教化与技艺渲染的艺术立场,走向了涉足人性和现代性的艺术道路。长期以来,中国戏曲在建构自身的艺术体系时,对于结束了古典辉煌之后所兴起的近代传统,往往看重其在人民性基础上的主题思想,对其更深层次的艺术创造并不能总览其详。特别是以京剧、粤剧为代表的戏曲辉煌与层楼再上,往往因为文学性的蜕变和表演性的更变,总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近代以降中国戏曲所形成的艺术成就。事实上,近代以来有太多作品在极速变化的时代转型间被埋没了光彩,梆子、川剧、汉剧、京剧等剧种取材于春秋卫宣公时期的题材即是一例。题材与人物关系的走向,本身就蕴含着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时代力量。《二子乘舟》的复排,让人们在挖掘京剧流派艺术代表作的同时,也更加有效地看到了京剧剧目遗产中足以代表近代传统、现代创造成就的光彩之作。

图2 《二子乘舟》剧照 (沈阳京剧院提供)
当然,该剧在此次整理演出中,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例如急子在听到宣姜被纳之后的气急晕倒,即进入到16年后的情节,剧情失去了表达其刻骨铭心的心灵悸动;公子急与宣姜新台会晤,宣姜主动试探公子急的动机需要更加清晰,由于此次整理一改宣姜惑乱亲情关系的言语行为,更需要对这一人物有所提升;夷姜主动赴死的震撼性亦显不足,更应与宣公的两次乱伦荒淫建立联系;剧终急子在公子寿代死之后,需要有更加充分的情感宣叙,更应突出其“心死”而走向生命死亡的必然性。此外,剧中的许多细节都应该紧密围绕道德人性的纯美与毁灭,每个角色的人性深度才能更加彰显出来。
这些侧面也说明了戏曲剧目的经典化,实际需要不同时代的艺术传承者们在不断的艺术提升中,给予更加理性与艺术化的创造,这才更加符合戏曲作为“活态”艺术的特征。从2001年开始,中国戏曲快速地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来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建,究其概念原始,“世代相传”“被不断再创造”“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与持续感”是非遗概念的三个重要内容,十多年的戏曲保护更侧重于戏曲世代相传的特点。其实,戏曲能够近千年来始终承载文化发展的重任,即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以及戏曲文化生态的生存力。戏曲经典剧目的不断成型,即是这种活力的艺术结晶。完全固着于“世代相传”,戏曲艺术遗产一定会与时俱损,毕竟艺术传承的核心在于人的创造性接受与传续,而非数量与形式的简单复制。《二子乘舟》在八十多年前创演之后,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唐韵笙重新整理,60年代再次修订,直到今天周仲博先生的加工改编,这正是一部新戏逐渐变“老”、变“旧”的同时,始终保持其艺术魅力而走向精致成熟的重要历程。
今天的老戏,就是昨天的新创。《二子乘舟》聚焦的历史题材,呈现的悲剧风格,展现人的人性深度和心灵世界,这些创作方法都完全迥异于京剧更早的艺术传统。如果参诸上世纪类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为代表的京剧杰出艺术家们所做的艺术实践,唐韵笙的这部新作不过是当时京剧创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如果参诸其时中国戏曲众多剧种在时代转型、家国危难之际所做的艺术革新,《二子乘舟》的创作与演出同样是中国戏曲引领时代风尚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部作品也成为戏曲改良到戏曲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探索成果,成为京剧追求现代性的一个代表性成果。今天,当戏曲界执着在“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选择时,需要对前此数十年进行的创新给予高度重视。在艺术史流程上曾经有较大拓展而至今仍然能够具有艺术震撼力的艺术作品,同样需要今天的人们去传承,同样需要今天的人们礼敬并延续它的创造性。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对于挖掘抢救整理传统剧目工作的重视,实际上将较长时间以来戏曲创作偏重于新编新创的风气,进行了更加合乎艺术规律的纠正和弥补。这当然是充分地张扬戏曲艺术传统、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工作,值得高度重视。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