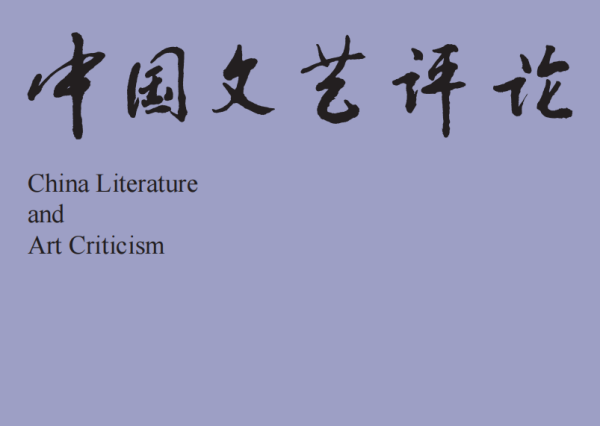
【编者按】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是新时代中国美育的重要课题。本刊特约请三位学者,分别从美学理论、文化研究、艺术史研究的不同视角切入,探讨美育更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意义,探究美育的知识构成与导引,以期进一步建构当代中国美育框架,继承发展中华美育传统的通达实践路径。
作为美育知识学导引的艺术史
【内容摘要】 美育是提升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养以及创造力与想象力的重要路径,因而在近些年颇受关注。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基础层面的持续推动下,美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而且在短时期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美育科研与教学系统。但就目前状况而言,美育建设与发展的基础环节仍旧存在可资讨论与辨析的问题空间,其中尤其显著的便是美育实施与开展的知识学基础与其导向问题。
【关 键 词】 美育 艺术史学 知识学 学科化
美育受到国内学术界、艺术界与教育界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美育逐渐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成为关乎国民精神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这条“逆袭之路”实则映射的是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节节攀升。这正是美育本有的逻辑。愈是物质条件丰盈、经济基础雄厚,美育的价值及其对于社会民众的意义也就愈加得到突显。但是目前,我国的美育工作尚处于起步与打基础的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旧不在少数。归总起来,诸多表征所共同指涉的问题之一便是美育的知识学问题。无论从何种角度加以理解,知识学其实都是一个基础性问题,既关涉学术概念、理论与基本议题,又直接地影响到教学系统规划以及培养目标的设定。而作为多个学科汇聚的交叉领域,美育尽管展现出不俗的跨学科适应能力以及多样化的知识生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自有学术根基与学理依据的薄弱。何为美育?如何美育?实施路径与评价标准为何?这些问题仍旧莫衷一是、悬而未决。显然,美育尚缺乏一种必要的专业性自洽,而通常是“因地制宜”地依存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与教学经验之上。因此,对于美育知识学问题的讨论无疑是必要的,而且也切实地影响着美育的体系化建设、教学与科研的系统性规划,以及健全美育长效运行机制等工作。进言之,探究美育的知识构成与导引,建构起符合美育诉求的知识生产与教学实践的目标方向,并且依此处理好各学科关系,促成彼此之间的合力,也就成为现阶段我国美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美育的当代症候及其表征
近年来,我国美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研与教学团队,以及囊括各个培养层级且兼顾社会性美育的庞大系统。转瞬之间,美育事业可谓焕然一新,充满勃勃生机,与以往的只言片语或零星散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如此这般规模化发展的背景下,美育自身所暴露的问题也更加明显与突出。
美育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这一方面表现为居间属性,即是说,美育是一个存在于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之间的中间地带,既涉及自上而下的观念导向,又关乎自下而上的现实反馈。而另一方面,美育具有跨学科属性,是由美学/感性学、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共建的交叉领域,关涉的问题域及方法论盘根错节,不可谓不复杂。这些特性构筑起了美育规模宏大的话语体系与知识系统,并且造就了多种学术生产机制以及教育技术与模式并存的局面。因此美育的问题症候必然牵扯多个方面。这部分地体现为学术科研与教学实践的脱节,部分地体现为目标方向的不一致乃至相互抵牾,还有部分表现为关键概念、主旨对象以及应用范畴的模糊不清。诸多问题及其表征固然与美育的独特性密切相关,但是对美育理解与认知上的偏差也是种种问题产生的关键原因。笔者以为,后者显然比前者所占比重更大,更具决定性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美育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得尤其显著。
首先是在学术科研方面。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仅在2021年发表的美育主题的学术论文就有4143篇,如果将“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等相关主题涵括进来,总数将达至万余篇。该项数据较五年前增加了一倍多,彰显出学术界对美育问题的关注以及在科研方面的增长力。但是问题也同样显著,所有论文分布在二十余个二级、三级学科中,占比较大的学科包括文艺理论、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影视、文化经济以及各级教育与教育理论研究等。显然,有关美育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较为分散的态势,多是依据每个学科的专业视角来谈美育问题。比如基于绘画、书法、音乐等专业特长来谈及美育的教学方法及实施路径,抑或从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角度来对美育的理论问题加以解析。这番看似繁盛的学术景象,实则潜藏着一个学术生产的合法化问题。即是说,作为目前的热点,美育这块极具发展力的学术公田,大多需要依靠外部力量,以其他学科的专业概念、术语以及观念与逻辑来做讲解,但专注于美育的对象、范畴及知识体系与话语系统等本领域的问题研究较少。
这一问题在国内高校的美育课程中有着更为直观的表现。就现阶段来看,开设美育课程的高校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艺术类的专业院校,其二是综合性的普通高校。艺术专业院校在美育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这些院校汇聚了从事各门类艺术的师资人才,而且配置有展览馆、影音厅等艺术展演空间,营造出极佳的美育教学环境及审美体验的艺术氛围。据此宋修见指出,专业高校浓厚的艺术气氛,近距离“触摸”各门艺术的便利条件,以及各类型的专业性论坛讲座与艺术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美育资源与潜移默化的美育契机,为美育学生的“专业成长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专业资源上的诸多优势无疑确保了艺术院校优质的美育教学环境,这是综合性高校难以企及的。但是问题同样显著。基于以往的教学经验,美育被理解为艺术的技巧与技能培训,抑或也将艺术鉴定、活动策划以及艺术市场管理归为美育的主旨。如果就美育自有的概念及功能属性来讲,即“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着眼于促进个体的审美(感性)发展,激发生命活力,提升情感境界,培养创造力,最终与其他教育一起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专业技能培训至多仅是美育的一个局部或构成要素而已。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其目标终归在人的精神与素养培育,这绝非是在技能与技巧的“术”的层面能够达成并实现的。笔者以为,艺术专业院校的职能并不在教育实践本身,更加重要的应是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只不过要突破“术”的局限,为美术教育专业增添人文与感性精神的维度。如果紧守“局部美育”的观念,那么在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培养层级以及社会大众领域中,美育也就会始终停留在“术”的层面了。这与“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主旨目标是有所偏离的。
与艺术专业院校有所不同,综合性普通高校一方面存在技能与技巧上的短板,另一方面又在健全完善的人文学科配置上具有绝对优势,所以一般是以人文通识性教育为着眼点,进行理论性讲解及知识性传授。通常情况下,综合性高校美育的起点是美学。这是由美育的学理逻辑及其源起之际的领域归属所决定的。自德国美学家、诗人席勒于《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1795)中首次提出美育概念开始,便与美学保持着亲熟关系,并且持续存在于美学的话语系统中,较多涉及到诸如审美精神与人格健全、审美理想与真理观以及平衡感性与理性精神等重要议题。国内学界也延续着此种模式,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至今的三次美学热潮的洗礼,有关审美教育或感性教育的学术讨论几乎均来自于美学领域。因此目前综合性高校的美育教学工作,往往是以美学为基础,链接与之相关联的“文史哲艺”各人文学科,继而构成多学科融合的教学团队以及囊括多方面知识要素的培养体系。比如华南理工大学较早开设的“大学美育”课程,即是以美学理论知识为导引,再分别就绘画、诗歌、戏剧及艺术哲学与建筑美学等内容加以讲解。再比如南京大学开设的“美育工程核心课程”,将重心放置于审美素养与人文素养提升上,分别设置有“视觉人文”“文学人文”“戏剧人文”“音乐人文”“媒体人文”“工艺人文”六个课程单元,并且配合课堂知识讲解,设置有不同的实践性体验课程。所以,综合性高校的美育教学强调从“知”的层面着手对不同审美对象的理论分析与知识讲授,但是在艺术技能与审美体验上则有所欠缺。
除上述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从心理学与教育学角度开展的美育研究,以及诸如博物馆、美术馆与各类型艺术剧院等专业机构开展的社会性美育。这类美育往往是浅尝辄止的,还缺少学术研究的深度及教学实践的持久性与稳定性。所以,艺术专业院校与综合性普通高校是目前国内高校美育的两股主导力量。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侧重,并且依据话语体系、学科倾向与课程主旨等方面的不同,在美育的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看似殊途同归,于不同层面、角度施行美育之事,但实际上彼此之间较少形成有效的互动与融合。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即是国内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关系在美育领域中的映射与延伸。但是比较起来,更为关键的应归结为各界对美育及其跨学科属性的理解偏差。诚如周宪所指出的:“从学科间关系来看,美育显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性的知识或教育领域。这倒不是说美育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及其合作来研究,而是强调美育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学科的知识要素,美育共同体成员必然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构成,这既是美育知识生产和教学的内在要求,亦是美育共同体构成的知识学基础。”总而言之,美育的科研系统及教学体系固然是由不同学科组成,是由不同专业群体的专家付诸实践的,但是绝不意味着可以置美育共同体而不顾,继而舍弃美育本有的逻辑及其赖以存在且有效发展的知识学基础。
二、学科化美育及其知识学基础
学科化可谓是关乎美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上述诸问题症候,既有学术科研也有教学实践方面的,均缘于美育的向心力或约束力不足,因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理解美育就显得尤为必要了。特别是在目前崇尚跨学科的整体学术环境下,明确自身的学科身份归属以及学科知识的专业界分,不论对于美育还是其他人文学科,皆具有基础性意义。
学科是在大学中设置的特定研究领域或专业科目。学科的专业划分来自于现代化社会分工,同时也是现代大学体制崛起并得以确立的现实表征。一方面,伴随机械化大生产推动的工业转型以及启蒙运动对现代理性的推崇,传统宗教价值观与信仰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致使社会发生较大规模的变动。依据韦伯的诊断就是,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崩塌导致了世俗社会的价值领域分化,继而形成了阶层划分及社会分工。学科化建制即是这种变动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学科化与科学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自然哲学的终结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逐步促成了以“科学”(wissenschaft)理念为导向的德式现代大学体制的确立。此一概念有别于英国或法国的“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既有哲学的形而上学意味又贴近于现实,同时也彰显出作为人的伦理理想与理智理想。因此那些本不具备狭义“科学性”的领域也被编排或归类为各式“学科”。诸如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皆因附加上wissenschaft的尾缀而成为一门科学学科。不过,在经过英美国家的矮化及庸俗化之后,即剔除了其中的哲学与伦理价值,“科学”概念随即成为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将知识的确定性与可实证性作为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格罗斯与莱维特曾对此有过专论,并且对于自然科学的“僭越之举”——依据自然科学的逻辑来对各个学科领域进行高低排序——予以批判。他们指出,在自然科学的主导下,科学被划分为硬科学与软科学两种。硬科学是指提供切实可被验证的知识,而像历史与文学便被归入软学科之列,被认为是仅能在事实层面带来一种相对可靠的知识,看似高度智力化但却百无一用。在此种观念的影响下,诸多软科学被迫进一步细化与细分,以求通过缩小学科范围而达成知识与对象一一对应的实证关系。如今在人文学科领域倡导的跨学科合作、跨领域融合实质上便是对这种不断细分为狭小领域的现状予以回应。换言之,是对具有广义性的wissenschaft概念的复归。笔者以为,这里所讲的“学科化美育”也是就此概念层面而言的。
在20世纪80年代,盖蒂基金会开展的名为“基于学科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的专项研究与教育计划,对于理解学科化美育颇具参考意义。该计划的出发点所瞄准的是对艺术及艺术教育的传统理解。通常情况下,艺术是创造性的,而且有诸多偶然性因素夹杂其间,艺术教育也因此被理解为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了。依据伯顿(David Burton)对全美中学艺术教育课程的调研,有近乎半数以上的教师较少或者完全不做教案设计与课程规划。个中原因自然同这种传统理解密切相关。而肖特(Georgianna Short)在调研中也有发现,教师在艺术教学过程中具有独断权,往往是依据自有的特长与专业背景来开展教学工作。而且,与国内艺术院校相类似,通常是以技能培训来替代美育教学。有鉴于此,“基于学科的艺术教育”便调整了目标方向,力图通过融合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史与美学四个具体科目来搭建教学系统,继而取代艺术教育原本松散、顺其自然的旧模式。该系统也就此作出说明:“正是通过这四个学科或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学生们才能把握到使艺术教育具有实质性和意义的内容。熟悉这些学科的内容可使学生用不同方式来关联艺术。”而且该系统还特别强调学科间的融合性,即是说,作为艺术教育的组成部分,“这些学科是相互重叠并交织于一体的”。进言之,艺术教育并不是教授艺术,而是关联艺术却又独立成系统的。尽管国外的艺术教育与美育存在一定的差异,概念、范畴与目标均有不同,但是无论在问题表征还是解决路径与方向上,两者却具有高度的逻辑同一性。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美育也在课程结构、观念理路及教学实践等方面存在着顺其自然的情况,而且各学科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离散状态。显然,学科化美育是一个解决各类问题的总的方向。
美育学科化绝非狭义上的学科细分,亦非依据各分支学科特长进行专业化美育发展,或者进行美育的科层化建设。相反,学科化建设应在明确美育自身特点及目标愿景的基础上,着眼于各分支学科的学科间性,继而形成多学科相互指涉且关联紧密的总体架构。教育部曾对高校美育目标有过说明,即“针对学生美育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建构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而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发文中更加明确地要求美育要达成“育人成效显著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升”的预期目标。由此可见,美育的主要目标在“审美和人文素养”,并非在某个方面拥有专业特长或者促成技能上的熟巧。这与美育的本意以及彼时席勒所讲的“感性教育”的定义相吻合。于此而言,美育的学科化建设便不是个把专业学科的事情了,而是要充分并广泛地联系到艺术、审美、信仰、情感、理想、道德、价值等问题领域,遍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部分。作为“关于人和人的特殊性的学科群”,现代人文学科同样缘起于19世纪的德国,与科学学科的概念密切相关,因此亦被写作“Geisteswissenschaften”。依据狄尔泰的分析,这种被称作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知识领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即“事实、命题、价值判断与规则”,分别指代感知实在的历史成分、抽象实在的理论部分与预定规则的实践部分。由此来讲,美育的学科化建设,以及支撑起学科化美育的知识学基础必定是多元复杂的。诚如周宪所讲:“对于大学美育来说,理论上讲应该有更多的学科参与进来,而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则应视作美育的四个基础性学科。除此之外,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应该作为美育的外围学科参与到美育事业中来。”
归结起来,美育的学科化建设可以理解为向“前学科性”的知识领域回归。杂多但却不失联系、繁复而又不乏主干。所以,学科化美育的关键即在于把握主导方向,抑或探究能够串联各分支学科、规划统筹美育体系知识结构的总的导引。

学生在博物馆上美术课(来源:“美术报”微信公号)
三、作为知识学导引的艺术史
美育绝非大而化之或随意而为的事情。但是依据美育的受众群体及其知识背景,美育却不得不降低其所辖各分支学科的专业性,借此来达成或从根本上提升美育可资接受的程度。尽管这里存在一定的矛盾,即兼顾美育的学科化发展与分支学科的去专业性,但是这却是居间与跨学科的美育的内在要求以及实施美育的现实诉求。
杜卫曾指出降低专业度及提升“参与性”对于美育的价值所在。“作为通识教育的艺术课程,面对几乎是零起点的学生……让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西洋音乐的学生首先面对巴赫的作品,很可能使他们那么一点宝贵的好奇心彻底泯灭,从此对西洋音乐望而却步。”这也就是说,美育实施的起点是审美对象及方式的通俗易懂。这就要求开放专业边界、降低专业门槛,凭借生动活泼的审美现象或艺术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开放与降低的程度及标准,何种类型与属性的对象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又或者是在什么样的语境或教学场景下,才能够使学生切实地获得审美体验及心灵上的感性滋养。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仍旧是见仁见智的,一种普遍的适用性标准似乎实难形成。基于此,麦肯(Penny Mckeon)从效果以及应用性角度对美育专业标准的讨论颇具参考意义。与前述观念相近,麦肯在参与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未来如何应用美育知识与经验的问题,即所谓美育的“前瞻性”价值。麦肯指出,虽然大部分审美与艺术教育是在艺术家工作室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有效地参与艺术实践并逐步积累个人的审美经验,但是这些所学与所感通常在毕业后并不会得到延续,而且也缺少必要的应用场景与实践契机。接受审美教育的学生,终归很少会成为从事原创性工作的专业艺术家。相反地,在毕业之后,他们多会进行理论意义上的审美与艺术活动,诸如参观博物馆与美术馆,到画廊购买艺术品等。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育经验在学生未来生活中的调用与输出通常是理论或知识属性的,而非实践性的。基于丹托的“艺术界”以及哈贝马斯的知识论与公共交往理论,麦肯明确地指出,美育最终是通过审美感与艺术感来实现其价值的,绝非是形而上的美学理论或者纯粹的艺术技能实践。那么,这种“感”的形成则有赖于“艺术理论的氛围和艺术史的知识”,因而应将艺术史而非其他专业课程视为美育或艺术教育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在课堂上讲解康德、黑格尔或者席勒的美学名作,学生们多会不知所云、面面相觑;而哪怕是面对最基本的艺术佳作,比如齐白石、徐悲鸿或赵无极等,如果没有必要的艺术史知识作为铺垫,不知所谓的情况也不会在少数,领悟作品中的创造力、想象力与形式美感也更加无从谈起。因此,介于哲学美学与艺术创作中间层面的艺术史,毋庸置疑地为美育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同美育的属性相通,艺术史学也是一门以综合性见长的交叉学科,不仅兼顾着哲学美学及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问题,而且还广泛地涉及形态各异的艺术对象及现象。但是这种综合性绝非像现阶段的美育一样,成为发散型的公共知识领域,而是有着明确的学术旨意与目标。基于众多对现代艺术史学的重要阐释,该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将讲不清道不明的艺术创造及感知问题,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转化为具有客观依据且可普遍传达的知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重要学者陶辛(Moriz Thausing)就曾指出,艺术史学是类同于“解剖学”的一门精准的分析科学,而并不是单凭个人好恶及独特的趣味准则来讲述艺术的故事。因为“充满主观性的趣味标准终究无法成为艺术史研究的核心……趣味判断所收获的永远是相对价值,极不稳定,因为趣味总是伴随时空而发生变化”。而施玛索(August Schmarsow)则更为直接地表示,艺术史学就是“将艺术显现的感官特性,以智性概念的模式予以呈现”。由此可知,艺术史学实际上是将艺术现象的杂多及审美趣味的个性化,凝练为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进一步地,经过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不断深化,艺术史学一方面形成了以风格、形式、视觉、观看、语言等为核心的概念矩阵及问题域,另一方面又构成了以形式分析与图像研究为主导的方法论系统,为呈现暧昧不清的艺术与美感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与话语系统。其实不难理解,居间的、跨学科的美育所需要的,正是艺术史这种既非纯理论又非纯实践的知识性内容作为基础。
事实上,艺术史学与美育本就具有很强的历史关联。同席勒美育观念提出的时间大致相当,建构科学严谨的艺术史学的自觉意识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开始蔓延。两者不单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与原生语境,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彼此交织、相互渗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征莫过于现代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作为文化传统及文明象征与传承的公共空间,博物馆与美术馆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职能,并且被视作一种国家性事务。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博物馆与美术馆迎来了大规模的发展,一系列重要场馆也悉数登上历史舞台。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基础工作是古物研究以及艺术品的收藏与展示。进言之,它不单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生产、传播以及公众的艺术与审美教育。就知识生产与传播而言,博物馆与美术馆实际上成为了艺术史学的策源地。经过粗略的观察便可发现,大多对后世影响颇深的艺术史学者其实都具有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职业背景。鲁莫尔是普鲁士政府筹建公共艺术博物馆规划的顾问,瓦根是柏林绘画博物馆(Berlin Gemäldegalerie)的馆长,艾特尔贝格尔是奥地利工艺美术博物馆(österreiches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的馆长,陶辛是阿尔贝蒂娜博物馆(the Albertina museum)的馆长等等,还有担任部门负责人或者从事收藏、策展等具体工作的艺术史家不计其数。有别于艺术史学根植于高校的当代机制或模式,彼时的艺术史是在与文物、艺术品的直接交往中发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后才逐步地影响并介入到大学中。诚如施洛塞尔在评价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时所讲:“我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四十年来始终恪守这一传统。这是高校与博物馆之间建立的富有成效的联系,最早出现于维也纳。艾特尔贝格尔的伟大创造就在于为高校教师建立了这样一个培养基地。”那么,反观公共教育,博物馆与美术馆又通过各种类型的艺术展览、学术讲座以及相关的期刊发表等,建构起了艺术与审美教育实施的基本路径与运行机制。相比于席勒以来美学话语对美育进行的纯粹理论性讨论,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则显得更具现实性,将提升感性精神以及恢复感官感觉能力的诉求带入到实务性层面加以实施。由此可见,艺术史与美育本就关系紧密、互为连理,不过是一方在行知识生产之职,另一方则是将艺术感与审美感通过知识的形式在大众层面上的传播与教育。
如果更进一步,即可理解艺术史与美育在深层的逻辑构成上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换言之,艺术史学是美育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与学理依据。一方面,艺术史为美育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概念与术语。从各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与审美理想,到不同艺术的感官感觉方式,再到各门类艺术创作的原理与方法,甚至是在教学规划与日常教学实践中所涉及的概念与术语,皆源自于艺术史的研究成果。诸如形式、风格、比例、透视、节奏、气韵、意象等各类术语,实际上正是从艺术史领域借取,并且跟随艺术史研究的进深而持续进行调整的。另一方面,艺术史是美育课程规划与设置的重要依据。在美育教学中所强调的参与性,或者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课程设置来调动学生的热情,对于深与浅、表或里的程度判断也是以艺术史学为依据的。具体而言,美育课程的设置及其逻辑依据,诸如哪件作品具有典型性、哪位艺术家具有代表性,以及艺术作品缘何呈现为这般状态,美学精神如何体现并有序传承等相关问题均无法独立于艺术史的判断而任意规划。换言之,在设定美育课程体系时,我们实际上调动的多是艺术史的知识要素,而非其他。相较于上述两个方面,更加重要的则在于,艺术史学绝不是处理艺术与审美问题的一门专业技能,而是普遍联系到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学科,编织出一张具有广博性的人文精神之网。比如李格尔(Alois Riegl)提出的“基于人的意志的艺术创造力”、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提出的“形式与视觉想象的发展史”或者德沃夏克(Max Dvořák)提出的“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均是将艺术问题置于广阔的人文精神语境中加以理解。所以才有了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的著名论断。在此意义上,艺术史实则成为了串联各人文学科的重要导引与纽带。而且对于美育的建设与发展而言,亦即增强美育专业的自主意识以及学术与教学上的约束力,艺术史也具有奠基性意义,不仅能够将存在属性差异及不可通约性的要素转化为艺术史的知识话语,并且能够通过理论建构合理地规划各人文学科在美育体系中的层级与位置。
结语:艺术史学进入美育
艺术史家克莱因鲍尔(Eugene Kleinbauer)曾指出过艺术史研究有着层级或内外之分。内部研究意指艺术作品鉴定或鉴赏,主要涉及作品的媒介材料、制作技术、作者身份、作品年代,以及对诸如艺术风格、形式语言、构成语法与图像意义等问题的分析与判定。外部研究意指艺术史与其他学科及方法论的交融,包括传记研究、格式塔心理学、符号学、经济史以及理解艺术家创作的思想史背景等。这种理解其实并不新鲜,在过往多有涉及与讨论。而克莱因鲍尔观点的重要性则在于,指明了内部艺术史研究是美育的基础或必备的工具,为教学提供了基本的知识要素,而外部研究则是美育的进阶,促使在思维与逻辑理路上对艺术感与审美感有更加深刻且全面的认知。这种由艺术史为导引的美育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及参考价值。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铺展及广泛介入,艺术创作与审美接受的传统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类型的新兴艺术模态及艺术大众化、娱乐化的发展趋向,不但降低了感性精神的比重,弱化了感官感觉的能力与敏感度,而且亦在逐步侵蚀甚至抹掉我们的文化记忆。因此,单凭各类艺术实践与体验实则难以调动学生们的参与热情,继而达成美育的目标愿景。由此可见,知识的价值与意义就当下而言是远超于艺术体验的,是重建感性精神、重塑健全的人格、推进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逻辑起点。当然,对于建设美育体系以及长效的运行机制来讲,艺术史学以其知识学导引的身份进入美育也是正当其时。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单列项目“19—20世纪德语国家艺术史学传统与核心概念研究”(项目编号:18CA1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毅 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7期(总第82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