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中国文化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epaper.ccdy.cn/zh-CN/?date=2021-05-13&page=3&detailId=%E3%80%8A%E5%96%9C%E5%89%A7%E3%80%8B%EF%BC%9A%E6%97%A5%E5%B8%B8%E9%A3%8E%E6%99%AF%E9%87%8C%E7%9A%84%E4%B8%AD%E5%9B%BD%E6%95%85%E4%BA%8B)
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场域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堪称是“横空出世”之作。他以朴素、传统的手法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描摹生活和人物本身的丰富与浑厚,复活、呈现并验证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魅力,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持续的冲击与震动。而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戏剧三部曲”收官之作《喜剧》则既延续了前两部长篇绵密、坚实的现实主义品格,又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尖锐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小说通过喜剧这一介于传统与现代的戏剧形式,关联广阔时代生活和不同人群,塑造了贺少天、贺加贝、潘银莲、南大寿、万大莲、贺火炬等各具特色的典型形象,从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维度完成了对当今时代各种荒诞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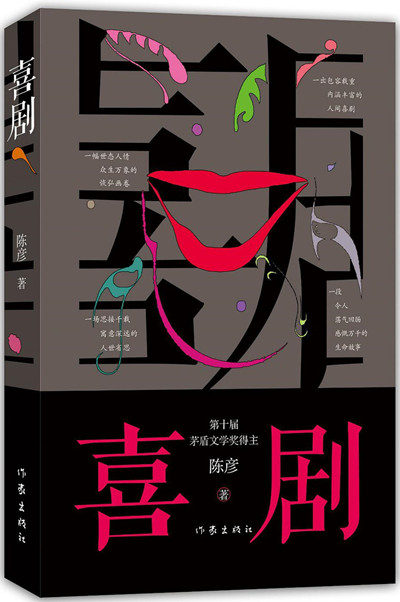
《喜剧》是一部兼具“戏剧性”与“日常性”的小说。一方面,叙事动作性强,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充满传奇性。小说保持了戏曲戏剧对语言和动作描写的重视,注重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情感状态,尤其是对人物内在心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冲突性有着丰富细致的表现。相貌丑陋得不凡的丑角父子三人,贺加贝带荒诞悖论色彩的命运遭遇,贺少天对喜剧时代即将来临的预言,贺氏父子的绝活儿,贺加贝对万大莲始终不渝的单恋,潘银莲的忍让、包容,乃至万大莲与潘银莲难分彼此的长相容貌等,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带有程度不同的超越生活常见形态的传奇性。而通过巧合(如万大莲与潘银莲容貌的极端相似)、突转(如当贺氏父子喜剧演得热闹红火时,贺少天被发现已是癌症晚期;贺加贝在高档别墅区买楼时,万大莲恰好因丈夫的犯罪行为而逃离别墅)、误会(如贺火炬因对贺加贝、潘银莲夫妇的怀疑和不满,而发生兄弟失和、叔嫂矛盾之事)等艺术手法,小说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更是不断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喜剧》又注重呈现“戏剧性”背后的“日常性”,尽力避免因人物事件的离奇性而造成不真实感。作家将笔墨和笔力集中于平凡人物的现实人生,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现人的命运遭际,揭示作为“社会典型”而非“抽象人性”的人物之内心世界,表现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内在戏剧性”,书写生活和人的“不奇之奇”。贺少天是闻名遐迩的“大艺术家”,贺加贝、贺火炬兄弟虽然比不上父亲,但也是广有影响的著名丑角演员。作为现实中的人物,他们的相貌、扮丑技艺和绝活儿,无疑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传奇性,但作家没有刻意突出其荒诞怪异,没有夸大这种传奇性神秘性,而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平常的人际关系、矛盾冲突,在世情和民情的层面和向度上,自然而然地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不无烦恼、痛苦和无奈的人生体验。
《喜剧》又是一部在现实性、历史感和真实性等方面带有典型的陈彦气质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以饱满、厚重、细腻的笔墨写出了当今中国日常性、社会性的广阔“真实”:通过丑角人物的行迹、遭遇,写出了戏曲在当下现实中的命运;通过丑角、喜剧所关联的广阔的城乡和更广泛的人群,写出了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真实;通过人物之间的爱情、亲情、家庭、婚姻等,写出了当下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的真实。当然,作家并不满足于这种日常性层面真实感的表现,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日常性的层面和境界,他试图通过超越经验性的现实描述,进入另一个世界和境界。这表现在,其一,小说通过贺少天、潘银莲等人物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情感结构。贺少天寄托着作家对喜剧之为喜剧的“本”性思考,小说通过他,侧重于从艺术方面证明戏剧要契合时代变动中的国人审美趣味。潘银莲从艺术的现实基底意义上,构成对喜剧/戏剧的“根”性观照,小说通过她,侧重于从生活方面证明,喜剧/戏剧要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经验。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戏剧如何变革,都要守持艺术(美)之“根”之“本”之神髓或更本真的生活与生命形态。如果说,贺少天与《主角》中的“忠孝仁义”和秦八娃一样,代表的是一种面对时代挑战却又生生不息的艺术美学传统,那么潘银莲则类似《主角》中的忆秦娥,代表着一种遭受现实挑战却绵延持久的伦理道德传统,他们分别在伦理和审美向度上蕴含作家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思考。同时关联伦理与美学两种“传统”的人物是贺加贝,贺加贝与贺火炬在喜剧演艺问题(实际上也是喜剧在现实中的“演绎”)上的歧见,贺加贝与潘银莲在感情、婚姻、家庭问题上的矛盾,则突出了现时代社会现实中“审美/艺术”和“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分流、分化与分歧。就此而言,贺加贝是一个叙事结构中的网结,也是传统说书艺术或民间说唱文学中的“扣子”。作为文学形象的“贺加贝”,是一个体现着作家“结构意识形态”的人物,他是“形式”也是“内容”。换一个角度看,在审美/艺术问题上,贺加贝与贺少天、贺火炬形成对照;在伦理道德问题上,贺加贝与潘银莲、潘银莲与万大莲、潘银莲和她的嫂子“好麦穗”同样形成对照,这何尝不是一种兼具“形式”与“内容”的戏剧性设置?其二,由日常性生成荒诞感,揭示存在于常态生活和生命中的荒诞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喜剧》是现实感与荒诞感的融合。小说扉页关于喜剧/悲剧、虚构故事/对号入座的表述,便是这一荒诞/现实的直观表述。通过强烈的戏剧化场景、细节,《喜剧》揭示了现实中的怪诞体验和荒谬感受。如贺少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不仅完全有违逝者初衷,更因过于郑重其事而又喧嚣闹哄而几乎变成闹剧,此可谓悲、喜、闹难辨。再如贺加贝对万大莲痴情不改,却不断落入与若即若离的万大莲共同编织的“心造幻影”中,此可谓真假难辨、“虚实相生”。贺加贝、潘银莲夫妇本意为贺火炬做长远规划,却遭到后者的误解,兄弟阋于墙。著名喜剧编剧南大寿经历屈辱后放弃喜剧,最终以散文家和动物保护协会名誉顾问闻名于世。传统喜剧没落后,喜剧笑点和“包袱”要靠电脑和数字模型计算出来;葫芦头泡馍生意红火的老板王廉举转行喜剧演出,历经大红大紫,最终落得街头卖艺,等等。红火与塌火、快乐与悲伤、痛苦与欢乐,彼此轮换、纠结、缠绕。可谓日常中的荒诞,充满荒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中的常态”而已。《喜剧》的荒诞源自生活经验和个人生命体验,是生活、世态中的荒诞一面使然,蕴含作家对现实社会和世道人心的体悟和理性认知,体现着作家对世间之人与事深感可笑、可悲或可悯的态度,由是在文本中生产出杂糅幽默、讽刺、戏谑、调侃、夸张等包含复杂意味的喜剧效果。《喜剧》的荒诞感是生活、人性、世道人心中的荒谬、荒唐、怪异的文学表现,属于我们所在的当代现实,有着民族感、历史感、现实感和时代感。小说以荒诞、魔幻的形式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现实机理与肌理。那些不合常情常理仿佛不正常的不可能之事,以乖谬、歪曲或荒诞的形式发生与存在,而它们对人物的命运轨迹起着根本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构成当代中国暗流涌动的世情画面。看似夸张幽默、令人莞尔却又无可奈何的尖锐的现实,在陈彦笔下得到了兼具同情、反讽和批判的揭示。而小说中那只被潘银莲收养的流浪柯基犬,也颇有魔幻色彩。柯基犬令人心酸的坎坷经历,折射出现实中的残忍与残酷、无趣与无奈。通过柯基的“魔幻之眼”看到的同样是“现实”的荒诞。柯基犬的遭遇、见闻及其所关联的小说人物置身其中却不自知的“视角”,借由一种对照和反讽的叙述,提供了对现实和人性的具有弥补性效果的体验与认知。在此意义上,流浪犬的“魔幻性”提供的却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生活和人性景观,是一种生活中不为常人所关注的隐秘面。

《喜剧》还是一部充满对时代、现实严肃思考的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力量的小说。陈彦以贺氏喜剧的兴衰沉浮,通过编剧、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揭示喜剧与时代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展现喜剧的多种实践形态与内涵,表达对喜剧及其关联的现实生活和人性的严正思考。寓庄于谐,是《喜剧》的基本手法;“含泪的笑”是小说的基本美学风格;以杂糅写实、荒诞和魔幻甚至“元小说”手法(借柯基犬之口说出小说的情节发展和结尾),对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及令人痛惜、心酸之人事的讽刺与同情,使《喜剧》具有讽刺性写作的内在品质。《喜剧》以带有夸张色彩的写实形式,对现实中的荒谬和不合理进行真实“再现”,它“戏仿”、嘲笑也批判荒谬的现实生活。这样的讽刺喜剧,对于现实的逼真再现和对于道德价值的捍卫,所引发的是带有现代启蒙主义性质的笑声。《喜剧》是否定的、解构的,也是肯定的、建构的,其中有讽刺、批判,也有调侃、嘲谑和滑稽。这一杂糅理性与感性、清醒认知和感觉狂欢色彩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贺加贝、王廉举、史托芬、潘银莲等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贯穿小说的向上生长或向下探源的执着不息的精神力量上。
《喜剧》借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量,体现着共情的力量,通过人物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感同身受人物所处的情境、所遭遇的生活和心灵的困境,感同身受他们及塑造他们的作者所投入所倾注的情感和态度。同时,小说又没有沉溺于人物的心理、情感,而是由内心而向外延伸、辐射。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主观性,使情感走出封闭的内心而走向广阔而复杂纠缠的社会生活。正如《主角》没有停留在主人公忆秦娥的个人生命体验或其心灵世界中一样,《喜剧》同样没有聚焦在一位或几位丑角艺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而是通过喜剧这一艺术门类和丑角行当,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面向。如此叙述,既有共情,又暂且跳出了内心,减弱了内倾性,而多了一份沉静和通透。小说中的个人不仅是她或他自己,而是一个具有相对恒定性和稳定性的整体。这个整体或者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或者是传统文化、思想、道德和美学的艺人形象。在他们身上,陈彦表现了一种民胞物与的传统人道主义悲悯,和对其个体心理情感、生活命运的热切关注,同时,又在他们身上体验到并发掘更多的更丰富的东西——人性、情感、欲望等。小说中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属于人学意义上的人,但也都是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他们都有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格,也有时代性所不能涵盖的、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世俗性、历史性和文化性格。他们的遭遇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人都可能会遭遇的问题。小说在“问题”中塑造人物,描述他们应对问题的方式,由此在社会现实、时代生活和心理结构、情感结构之间建立呼应和联系。这种叙事方式,或可称为陈彦式的世俗心理结构分析。《喜剧》《主角》采用的便是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在地性”中国现实主义,不仅是贴着地面,贴着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和当下中国现实状况的思考,也是进入“中国之心”的思考。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艺评中国”新华号